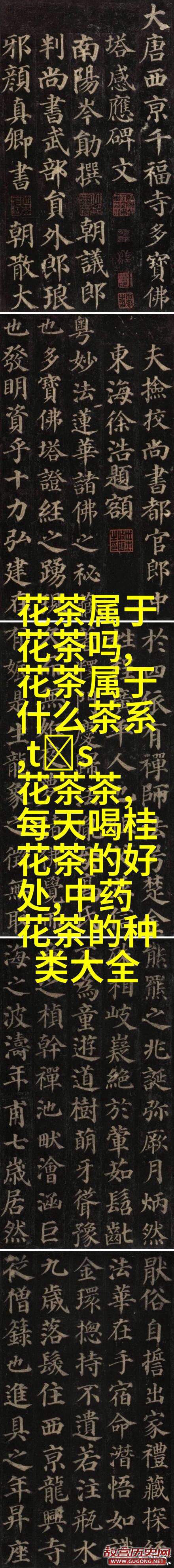我曾经在与朋友们共饮时,误将茶杯斟得满溢。其中一位朋友责怪道:“你说自己懂茶艺,却连基本的用茶规则都不知道。记住:酒满是敬人,茶满是欺人。”我本心中真诚,只因不谙俗礼,反而招来了责难。在这次喝茶的经历中,我既吃了一个教训,也学到了许多。

安溪人的传统是“知茶达礼,通酒感恩”。在待人接物时,我们总会运用“酒茶为媒”的繁复礼节,即使是在饮酒和品茗时,也要遵循一定的规矩。如果过于注重这些礼节,这确实有些让人感到压抑。但面对今天越来越重视礼仪交往的社会,你又不得不尊重自古以来的一些传统习俗。自古以来,酒和茶都是待客常备之物,也是待客珍贵之宝。这两种液体形象中的“礼节大使”,若处理不好,就可能会玷污你的形象。
酒与 茶,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,都有着深远的影响;无论是仕宦大夫还是平凡百姓,都需要借助它们来践行礼仪。然而,在这个过程中,便出现了敬人的意义与欺人的误区。在我们今天迎接宾客时,有时候也会因为这种误解而生出一些不必要的情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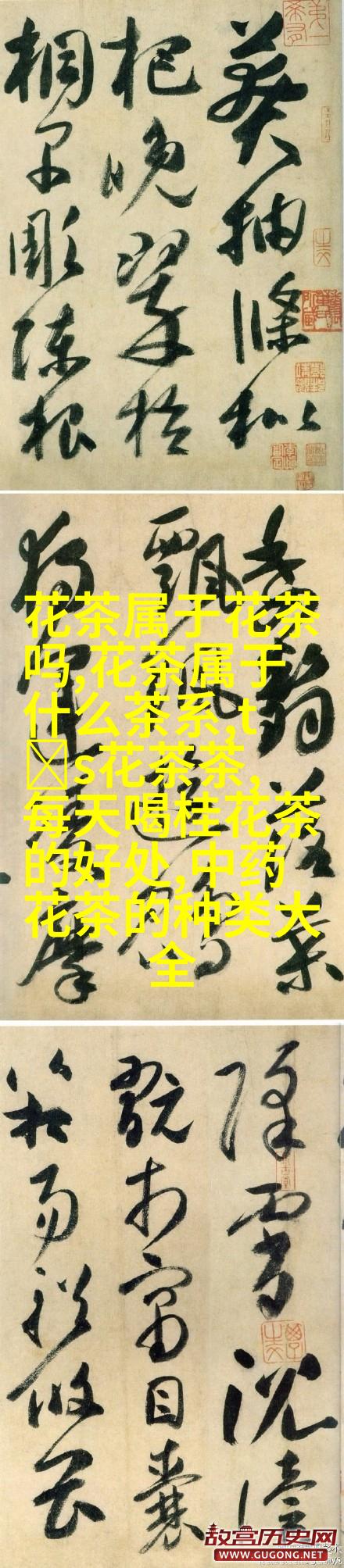
这样的说法真是不可思议。在从敬酒敬 茶 的相悖定律中,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例如,从如何清洗 茶垢就能窥见一二。此外,还有一句名言:“敬酒不吃吃罚酒”,这是否意味着主人对客人的热情太过头?或者,将文明的禮儀带入野蛮之地去了?安溪作为 茶 的发源地,一直以來都是僧侣會友的地方,每一次山間之樂都與 茶 相伴。而慧苑寺裡有一對門聯寫道:“客莫嫌 我當送您茗,不惜為您種竹。”這說的是寺院清靜遠離世事,用僅有的 范子 送給來訪者,用僅有的竹林作為鄰居,這就是對於生活簡樸、遠離世俗浮華的一種表達。而且,它們各自具有一定的特性:茗能收敛心緒,而醉則放縱欲望;茗柔順而力微,而醉則強悍卻易受制约。
因此,当我们为朋友们斟满一杯 茂趣 或者 一壶好 酒 时,又怎麼敢说那是一种欺骄呢?

恩格斯曾批评英国上层社会模仿东方の禮節時說過:習俗會把熱情導致死亡。我們應該適應時代變化,不過度拘泥於傳統禮節,以適應多元文化發展。一如鲁迅《烟雨》所描写北京胡同里的大碗茗待客,以及江南阿庆嫂家里的铜壶烧的大碗茲,以及安溪村庄里的青花瓷碟盛滿,再举起仰脖儿痛快地一饮而尽,那才算真正高兴。但那也是艺术,不代表日常生活。我們今日迎接宾朋,可以选择各种饮料,但仍旧不会忘记那两样看家的东西——它们决不会少去。你喜欢或嗜好不是问题,只要不是厚此薄彼即可。我五十年风雨兼程的人生旅途中,或许借助过 酒 来燃烧,或许借助过 茂趣 来冷却。但從養生的角度,我認為我們应该改变那个規則,让它变成这样:“烹飪滿瓶,是謀殺;裝填滿瓶,是祝福。”
不知诸君以为如何?